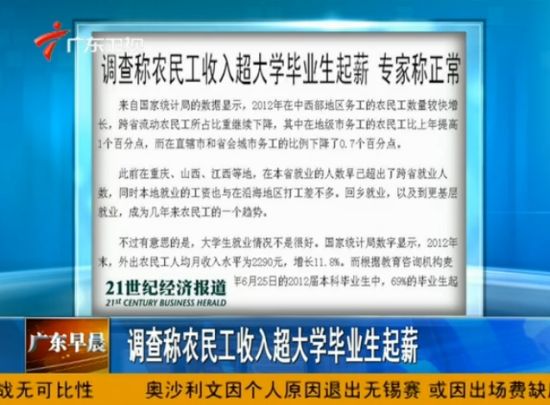看到像胡里奧這樣的古巴醫生、教師和市民們忙忙碌碌地操持他們的“新寵”——家庭旅館,我不禁心有靈犀地頷首微笑,他們和十幾年前的中國人一樣,喜歡“忙”。中國人現在應該說已經忙出了一些成果和財富,但也忙出了困頓、苦悶和迷茫。而他們,仍然處在追求財富的途中,充滿期待,干勁兒十足。
如今,旅游業仍然是古巴最賺錢以及賺錢最快的行當,拜近兩年出臺的“開放政策”所賜,好似每個城市、每條街上都比肩而立著數家掛有藍色“工”字標識的家庭旅館,每一家的屋前或陽臺上都放著一兩把搖椅,搖椅上或早或晚會出現一位叫“胡里奧”的小老板,等著幫你實現來古巴的每個心愿。
古巴的經濟學家堅持對媒體表態說:“我們不是在搞改革開放,而是經濟模式的更新。”我不知道二者的區別何在,不過每當看到古巴老百姓臉上那充滿期待的笑容,總感覺似曾相識,那完全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練攤兒”、“下海”的街頭小販的摸樣。他們對政府、政策的抱怨,在我們聽來多半有點小兒科,同時也不禁想起,不過就在數年之前,我們也曾經這么小兒科來著。
我以為,人生的幸福,就在于還保留著一絲較真兒的興致,那說明你對未來還有所期待。如今,古巴人羨慕中國人手頭有足夠的“活錢”,中國人則羨慕古巴人有從生到死,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體育……的全套免費福利,還有敦親睦鄰的溫暖人情。
古巴每年的財政支出,有一半以上是用于教育和全民免費醫療這兩項“社會主義福利”,古巴的醫療在世界上的聲望一直很好。胡里奧工作的地方是哈瓦那的一家普通診所,相當于中國的社區醫院,有很多個專科,有化驗室,X 光室、超聲波室等,不過沒有住院部,胡里奧說很多醫療設備是中國援助的。古巴的醫療體系大致分為三個層次:最低一層是家庭醫生診所,每120-150 個家庭有一名家庭醫生及至少一名護士,小病就由家庭醫生就近治療,嚴重的由家庭醫生提供證明,進入第二層——綜合診所,第三層就是有住院部的二級、三級醫院。
我曾在路上對哈瓦那的“市立醫院”有過驚鴻一瞥:前立面儼然是帕拉迪奧經典的羅馬建筑設計,那種堂皇,絕對堪當國家博物館的重任;粗壯的大理石立柱,讓人想起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門口有寬敞的停車空間,不過沒有幾輛車,就診的人不多,其中也沒有幾個是開得起汽車的。古巴每千人擁有5.3 名醫生,而剛被奧巴馬的醫改搞得全國上下沸沸揚揚的美國,每千人只有2.7 名醫生。古巴的多項重要公共健康指數始終保持在發達國家的水平,公民平均壽命78 歲,居拉美地區之首。
但是古巴人也有一句閑話:“在古巴,做一個心臟移植手術比得到一片阿司匹林容易,得到一個大學文憑比得到一支圓珠筆容易。”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胡里奧醫生要白天忙著開刀,晚上忙著開店。和古巴的律師、技術人員以及其他“專業人士”一樣,他的手頭也總是缺少那么幾個活錢。
作為一個生于70 年代的人,我對古巴心儀已久,有著特別的念想。對我來說,這個加勒比海島不盡然是一個“旅行目的地”,甚至不盡然是一個“國家”,它更多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是某些能帶回少年時代共鳴的心弦頻率。當我們這代人跌跌撞撞地在水泥叢林里奮斗過一陣,摸爬滾打地成長了一段之后,古巴,似乎成了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生活路徑、搜尋某種平衡感的入口。
古巴與中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它的現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我們毅然拋卻的過去;它的未來,又可能是我們的現在。它的存在本身,似乎還代表了一種價值感的回憶,代表了我們對某種“歷史潮汐”的期待和好奇,我們想要知道,自己曾經拋卻的是不是太多?是不是拋卻得太早?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