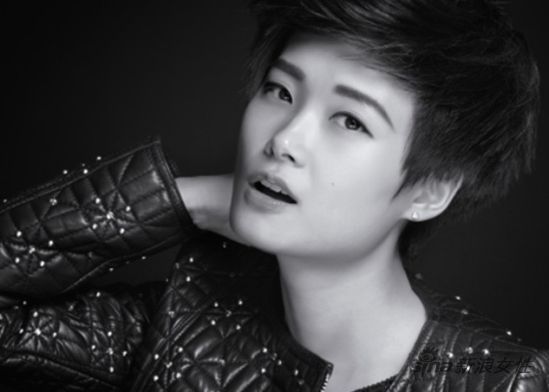在最后一個展廳,有別于之前的華麗,好幾幅巨大的黑白照片鑲嵌在墻上,全部都是二戰后被嚴重破壞的華沙老城照片。看來重建是為了更好地記住歷史。正當有朋友在照片前合影時,一個穿著工作服的白發老者走過來想和我們交流。原來,他想知道我們是否來自中國,因為他的女兒是一名模特,馬上就要到中國短時間地工作。此刻能在這里見到閨女未來的“同事”,自然有些激動。
離開皇宮來到老城的美人魚廣場,廣場中間立著一尊美人魚雕像。美人魚是華沙的象征,也是華沙的保護神,相關的傳說有很多。畢達告訴我們的故事版本是,從前一對打漁的夫婦,在維斯瓦河上捕到一只美人魚。美人魚懇求夫婦放了她,并許諾會終生保護他們。善良的夫婦放了美人魚,在華沙繁衍后代,而美人魚也成了華沙的保護神。不管哪個傳說是真實的,美人魚已經成為華沙人的精神支柱。廣場中間美麗的美人魚右手舉著刀,左手持著盾,似乎在保護著華沙。
“我是華沙人”
每年到肖邦誕辰紀念日時,人們會在古城舉辦一場連續7天,每天24小時的音樂會來紀念這位鋼琴詩人。7天內不論晝夜,都有人在排隊等待演奏,其中有著名的演奏家,也有平常老百姓,這都是自發的。
穿過廣場時,腳邊的鴿子一點都不怕人,肆意地在地上踱著步,等待人們喂食。跟著畢達我們像轉迷宮一樣,在老城里逛著,突然在一所房屋前停了下來。抬頭看到三層樓的墻壁上畫著一個婦女抱著一個嬰兒,嬰兒的手里拿著一支試管,試管里飄出了兩道煙,一道寫著Ra,一道寫著Po。此時我們已經猜出是和居里夫人有關。原來這個三層小樓是居里夫人的出生地,她在24歲前都居住于此。她的父母是沒落的貴族,來到華沙后,開辦學校當老師,因此他們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當國內大學不收女生時,她被送到法國上大學,后一直定居法國。為了紀念祖國波蘭,她在發現新化學元素時,命名Po。她每次演講第一句話總是“我是華沙人”。可見她的心中永遠裝著祖國波蘭。
另一位波蘭名人肖邦,沒能夠和居里夫人一樣出生在老城,卻將自己的心臟安放在這里——圣十字教堂(St. Cross Church)。逛完老城區再一次路過圣十字教堂時,畢達帶我們走上十幾級臺階,進入了這個神圣的殿堂。幽暗的室內,和普通的大教堂沒什么區別,零星的幾個人在成排長凳上做著禱告。在一個非常粗大的柱子右側,我們坐下來期待著波蘭人講肖邦的故事。“肖邦在波蘭出生,21歲時離開波蘭之后就再也沒能回來。當時的波蘭已被瓜分,作為一個愛國之士,迫于政治上的威脅和身體健康的原因,他到死都無法回到祖國。后人遵照他的遺言,將他的心臟帶回了波蘭,并安放在圣十字教堂教的這根立柱里。二戰期間,這棟教堂沒有遭到破壞,不知道和肖邦之心是否有關。”畢達壓低嗓子說著,并指了指左側的柱子。“柱子上的名牌寫著1810年2月22日,這是肖邦受洗禮時在教堂登記的出生日期,但他真正的生日是3月1日,相差一周。據說有可能是出生半年后,父親才去登記,結果記錯了日子,但是保守的天主教不允許修改,所以他有2個生日。每年到肖邦誕辰紀念日時,人們會在古城舉辦一場連續7天,每天24小時的音樂會來紀念這位鋼琴詩人。7日內不論晝夜,都有人在排隊等待演奏,其中有著名的演奏家,也有平常老百姓,全都是自發參與的。”
聽完故事,我們繞著大教堂走了一圈,畢達又指著一尊天使雕像說:“看到這尊雕像了么?如果你們上個月來,就看不到它。因為每分每秒鐘,華沙都在發生變化,我們在一點一滴地重建著它。”畢達的臉上表現出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豪。波蘭民族的骨子里有著一種驕傲和執拗,在那段被欺凌的歷史前,他們并沒有把它當做一種恥辱去刻意隱藏,而是面對現實,努力保存住自己民族的歷史,將曾經的破壞降低至最小。
教堂內的一個隔間里,人們在舉行著某個集體宗教儀式,波蘭人對天主教有著堅定的信仰。雖然曾經受到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基督教和俄羅斯東正教的各種影響,現在波蘭國內95%的人仍信仰天主教。即將要離開教堂時,我們發現一側墻上掛滿了密密麻麻的銅質黃牌,每一塊上面都刻了一些字。畢達給解釋說,這是人們表達感謝的墻,大家把感謝的話語寫在這里。他翻譯了幾個牌子上的內容,我卻只記住其中一塊寫著“我是一名來自奧斯維辛的囚犯,感謝上帝讓我活下來,編號26627。”
走出教堂我們路過哥白尼的雕像,畢達刻意駐足片刻,對我們嚴肅地說:“我想再次聲明,哥白尼沒有被燒死。”他在為他的同胞喊冤,因為我們幾個總把哥白尼與伽利略混在一起。“他得病去世了,所以宗教的人沒來得及燒死他。”畢達用幽默的口吻闡述這個事實,希望我們對這位“日心說”提出者有正確的認識。
“華沙速度”
波蘭在私有化之后,經濟得到了刺激,城市正在經歷融資、投資、建設和發展的過程。深處經濟危機四處爆發的時代,波蘭的GDP卻能以6%的幅度增長,這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難道不像嗎?
華沙市內的常見交通工具是黃紅顏色的有軌電車。這種車是波蘭自己研發的,因為物美價廉受到德國、匈牙利、捷克等歐洲國家青睞。目前華沙市只有1條地鐵,建于90年代,2號線正在建設中。市內繁華的地段,不時還能看到一片荒蕪的空地,有時上面會停泊很多轎車。畢達說這是因為國土私有化之后,有些地塊所有權沒有得到明確,所以只能先荒廢著。在波蘭,土地和房子所有權都是永久的。
聽著畢達談論著哪個地方又要蓋一棟最高的居民樓,哪個地方誰又要投資新建一棟寫字樓時,真的意識到波蘭與中國相似之處頗多。波蘭在私有化之后,經濟得到了刺激,城市正在經歷融資、投資、建設和發展的過程。深處經濟危機四處爆發的時代,波蘭的GDP卻能以6%的幅度增長,這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難道不像嗎?按照畢達的話說,華沙就像90年代的浦東,各類公司在這里投資發展。說起計劃經濟,78年出生的畢達又侃侃而談:“我小時候,只有六,七歲時,還幫我媽媽去排隊買東西,一排就要1~2個小時。那個年代需要用票才能買到米、油和鹽。物資都是定量供應,有些東西沒有個人關系,根本買不到。我爸爸很聰明,大家都為了買彩電在外面排長隊時,我爸就從隔壁賣雜貨的人那買了點東西,然后讓他們帶著直接進到隔壁店把彩電也買了。要知道一共才那么幾臺彩電,在外面排隊等著買,肯定輪不到。這種經歷和感受只有中國人和越南人才會明白的。”他說完無奈地笑了笑。“不過還好我們波蘭有了89年的轉變,90年代麥當勞在華沙開了第一家分店,我們也有漢堡吃了。我個人更喜歡89年后的波蘭,人們更加自由了。”
高230米的科學文化宮(PalacKultury I Nauki)始建于1952年,于1955年竣工,前面的閱兵廣場曾經是前蘇聯時期第二大廣場。這棟蘇式建筑是前蘇聯送給波蘭人民的禮物,據說當時斯大林給出兩個方案選擇,1.科學文化宮,2.是地鐵,而波蘭人民選擇了科學文化宮。科學文化宮由來自前蘇聯的3500個工人,按照前蘇聯人的設計建造。建造過程中,一次事故還導致16位工人喪生。這座建筑與前蘇聯時期的其他建筑非常相似,比如莫斯科國立大學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救世主塔。
被華沙人簡稱與“Peking北京”同音的科學文化宮PKiN并不被波蘭人所喜愛,因為它象征著蘇聯人對波蘭的統治。在波蘭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后,國內很多人都在討論是否要拆掉這座蘇式建筑,但是最終華沙人還是選擇讓它屹立在華沙市內作為標志性的建筑。原因有三個:一,它確實是一棟有特色的建筑;二,雖然波蘭人不喜歡這段歷史,但是歷史終究無法改變;三,保留著它,還能證明當斯大林已經消逝在歷史時空時,波蘭人還在自己的家園里安居樂業。“現在每任市長講話,都不會忘了說,‘我認為科學文化宮應該拆掉。’”一本正經的畢達講完這句話笑了,看來波蘭人民也有政治幽默。
現在的科學文化宮仍然是華沙市最高的樓,里面有電影院、博物館、辦公室和學校等等。波蘭資本化之后,所有單位都是自負盈虧,科學文化宮的一部分收入也來自辦公區的租賃。畢達周末偶爾會在這里教課,他可是國際關系和漢語雙學位的高材生。
我們乘坐電梯來到28層,華沙的全景展露眼前。對面的新玻璃大樓上張貼著巨幅辦公樓招租廣告,旁邊一棟被拆成框架的12層大樓正等待著重建,馬路上車水馬龍,霓虹燈的點綴下,華沙城一眼望不到盡頭。有著這樣的“華沙速度”,明年的此時,華沙該是另一番景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