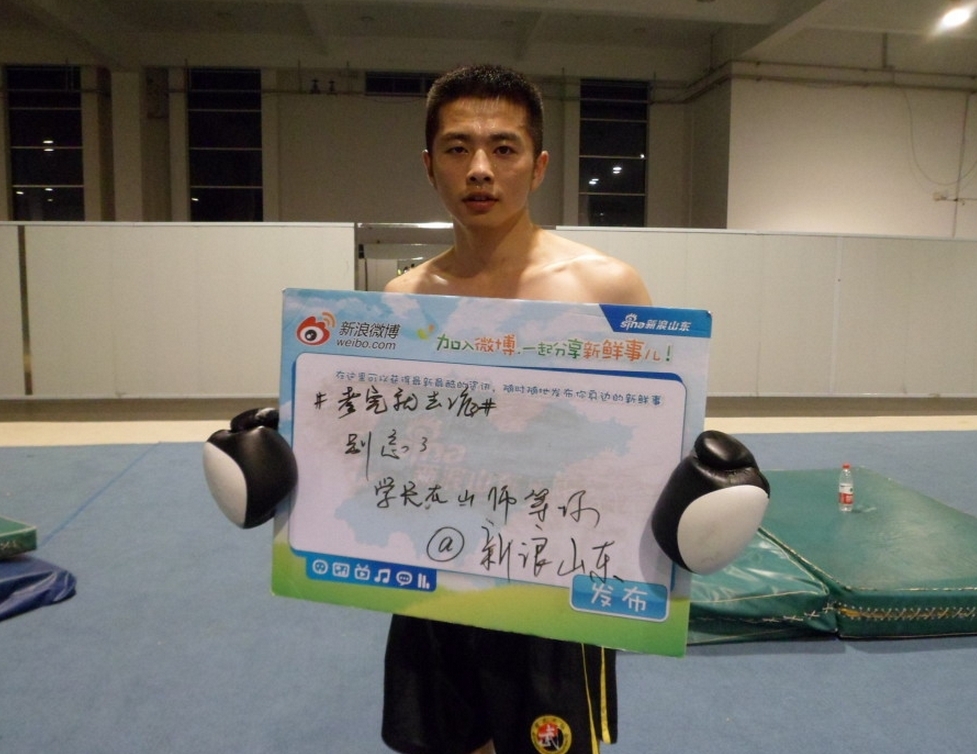��������Ĺ�@���Ӣ����䛉���
����6��12�գ��Ї��h(yu��n)��܊�ھ��鿹�������ʿ�IJ����z����Ĺ�صĉ����������b��24��(g��)�ǻҹޣ��w��������ʡ�v�_����Ĺ�@���Ї��h(yu��n)��܊�����ʿĹ���˕r(sh��)�����x�@Щ��ʿ�����h(yu��n)�������^ȥ��70���ꡣ
��������Ĺ�@�|���T�⣬һ������ʮ���L�ġ���䛉��������@Щ��(j��ng)�v�������h(yu��n)��܊�ϱ���������ץס�����һ�z���С������ѽ�(j��ng)�o���ٴθ�׃���\(y��n)���������ԣ�Ψ����ˣ��š����ܱ����ӛ���������w�ŵĕr(sh��)���У��҂�����(y��ng)ԓӛס�ģ�����(y��ng)ԓֻ�ǡ���䛉�������Щ�ϱ������֡�
�����������@���c�r(sh��)�g��ِ���У��vʷ�K���ٳ���
������/Ƭ ����(b��o)����ӛ�� ��־�� �l(f��)�������v�_
�����ϱ��x������ϣ�����h(yu��n) �͑�(zh��n)�т���һ��
����6��12�����磬�v�_����Ĺ�@���Ї��h(yu��n)��܊���������ʿ�������F(xi��n)�����f��(y��n)�C�¡��˕r(sh��)��һ�l������Ϣ������ԭ��Ҫ�텢�ӽ��칫�����(d��ng)���v�_91�q�ϱ����c������ǰһ�������x����
����12�����磬���v�_�h�I��С�^(q��)һ̎Ժ�䣬�ѽ�(j��ng)�����`�ã�ͬ��һƬ�C�¡�
�������������wһֱ�����e(cu��)�����������g���ˣ����w���(xi��ng)�����˻�����ͻȻ�x���ġ����Գ����ڱ�ʹ�еď����˸��Vӛ�ߣ����˱������Å���12�չ������(d��ng)�Ĝ�(zh��n)�䣬�]�뵽ج�ĕ������@ô�졣
����1923������ď��c��ԭ������ʡ������ƺӿh�����Ї��h(yu��n)��܊20���F(tu��n)܊20��վ���O(ji��n)��ʿ���������c��������ؕɽ���Տ�(f��)�v�_���T����(zh��n)�ۣ�����(zh��n)�Y(ji��)�����c���������v�_��Ȣ�����ӣ�����Խ̎��������ݣ��Ǵ�ǰ�v�_����������h(yu��n)��܊�ϱ���
������������������(sh��)�����ڵ��ϱ������c�����ݺ������һֱ���e(cu��)����ŮТ혣��Լ�ÿ��(g��)�����I(l��ng)��2000Ԫ���ݽ����ӿ����f�H�����e��
����������ˣ����������ĽY(ji��)�������h(yu��n)��܊�ϱ������顣���˃��Ӹ��Vӛ�ߣ����v�_�������e�k��Ƽo(j��)����(d��ng)������Ҫ���ӣ�2011�����v�_�e�е��״Ρ��һ�w�����D�D�h(yu��n)��܊�z���ؚw���ϣ����c�����M���ۜI�f����ʣ�µđ�(zh��n)�ћ]�ж��٣���Ҋһ����һ��ɡ���
���������˸��Vӛ�ߣ����^܊�˵ď��c��һֱ����܊�Gɫ�����b���Ъ�(d��)犣���֮ǰ�����Ђ�(g��)�H���ڹ����֣��ͽo��һ��(d��ng)�r(sh��)���Gɫ���Ĺ����Ʒ������˸��d�ò����ˣ��������촩������
�������c�������r(sh��)������ֹһ�α�ʾ��ϣ���@Щ����������^������Ŀ���(zh��n)�ϱ����܉�õ��J(r��n)�ɡ�
��������������ȥ���˼o(j��)��F(xi��n)���������`���ѽ�(j��ng)�S��(zh��n)��ȥ�ˡ������˃���ĬĬ���f��
���������f��������ǰ����ֹһ���f�^��ϣ���^�����܌��Լ������̵ֿ��v�_����Ĺ�@���h(yu��n)��܊��������䛉��ϣ�������ϣ�����܉����h(yu��n)�����đ�(zh��n)�т���һ�𡣡�
������䛉����C������(j��ng)�Ęs��
�����䌍(sh��)��ֹ�ѽ�(j��ng)�xȥ�ď��c���л����������h(yu��n)��܊�ϱ��������oһ�������@��(g��)Ը�����������ϡ���䛉����D�D�����J(r��n)��ֻ���ǘӣ�����ζ�������J(r��n)�ɡ���
�����@Щ�ϱ������f����䛉���λ�ڇ���Ĺ�@�|���T�⣬һ������ʮ���L�ĉ��ϣ��������������h(yu��n)��܊10�f���������ߵ����֡�
������Щ���������п��Ʊ�������֣����@Щ���˂����У��s��ζ��һ�α���q�¡�
�����������������@Щ���֕r(sh��)������6��11�����磬��Ĺ�@�ġ�������(zh��n)�ۼo(j��)���^����һλؓ(f��)؟(z��)�Ӵ���Ĺ�@�����ˆT���Vӛ�ߣ�������(j��ng)�Ӵ��^һλ������ص������Ѯ���ϱ�����(d��ng)�r(sh��)���˅��^����䛉����r(sh��)������?f��)���һ��(g��)��(g��)���֣���������¶���ĸ��飬���˿��˶���ޡ���
����������l���S�ɡ�������䛉����������˼ҵ���Ը�������̵ֿ���䛉��ϡ��������_�o(j��)���^ǰ�_�DZ������ϱ��Ӵ�ӛ䛣��@�ӵ����Ԏ��S̎��Ҋ��
�������Ҡ���ÿ��ȥ����Ĺ�@����Ҫ�м�(x��)���ǂ�(g��)�������ֵĉ�����11�����磬88�q�h(yu��n)��܊�ϱ���?b��o)w���ČO�ӏ��������Vӛ�ߣ���䛉����Ўοհĵط�������ÿ���ߵ��@�ﶼ���v�����á�
���������f��������䛉��������������J(r��n)�ɡ��������^ˮ���µ�̎��(zh��n)����91�q�h(yu��n)��܊�ϱ����w�䣬�M�ܿ��X�ѽ�(j��ng)��̫�`�㣬����ͨ�^��ϱ�D��ӛ���D(zhu��n)�_(d��)���@��һ��Ԓ��
���������@Щ90�q���µ����˂����ԣ���������ʣ�o�Ěq��������ѽ�(j��ng)�o��ͨ�^�Լ���Ŭ����׃Щʲô������ϣ��ͨ�^�@�N��ʽ���C���Լ�����(j��ng)�Ęs�⡣
����ӛס�vʷ������(y��ng)ֻ��һЩ����
�����@Щ�ϱ���ϣ�����ϡ���䛉�������һ��(g��)��������˼���ǡ�ֻ���@�ӣ��Լ����ܳɞ������Ěvʷ��һ���֣������������ӛ�������ǣ��������ˡ����������Ўׂ�(g��)��֪�������Ěvʷ��
�������ڮ�(d��ng)�r(sh��)�y(t��ng)Ӌ(j��)�l�����ޣ���(g��)�e��δ�������h(yu��n)��܊��(zh��n)ʿ��������Ҳ���̵���Ĺ���е���䛉��ϡ�
����12�����硰���������(d��ng)�Y(ji��)����ӛ�����������F�����x��74�q���˗���־�����Ķ������⟘���ο����h(yu��n)��܊��(zh��n)�Կ��A(y��)���(du��)��103����309�F(tu��n)���F(tu��n)�L���M�ܲ�δ�ڑ�(zh��n)���Р������������ԡ����ˉ�����
��������־�f��ֱ��ȥ��������Ҳ��δ���������^����(d��ng)�꿹�յ����顣����������ͨ�^��� ���Ŵ_���˶�����µIJ��(du��)��̖���ٺ���� �f�v�_���h(yu��n)��܊Ĺ�أ��^��һ��������������ѽ�(j��ng)��Ȼ�������@���һ�K���ϡ�
�������]���l��Ո�������X�Ñ�(y��ng)ԓ�^����������־�f�����������o���|��(d��ng)�ܴ������@Щ����һֱ����æ���h(yu��n)��܊�ϱ����£����J(r��n)���ϱ�ÿ�궼���ߣ��������ϧ���������������е��Ƕ����F�ġ��vʷ�����������S�L(f��ng)��ȥ�����M���@����ܿ������������֡�
 �Ї�������ô����ͧ
�Ї�������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