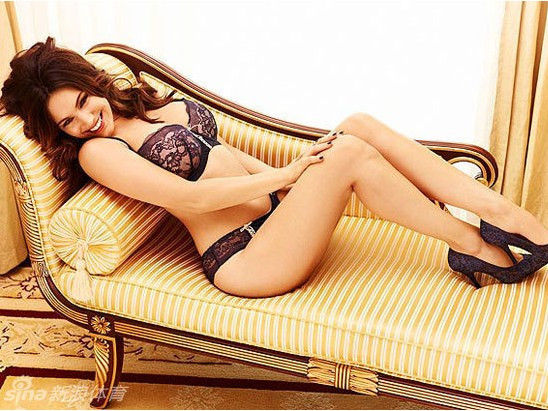于寧
1月11日,國家安監總局公布了山東青島黃島中石化特大爆炸案調查報告。時隔不到一個月,這一牽動全國人心的重大責任事故終于有了官方結論。在事故爆炸之初,財新網即派出記者于寧等人奔赴現場,在短短的數天之內,發回數十篇稿件和現場圖片,全方位地報道了這場人禍的前因后果。回顧記者的所見所感,仍能感受到當事人的悲慟與憤恨。逝者長已矣,而對于生者而言,安全管理、善后、問責的工作仍應持續下去。
——編者
以前別人問我,你們老做負面報道,看到那么多壞事情,不會影響你的心情嗎?我的回答一直是不會,因為我即使寫十篇劉志軍(原鐵道部部長)的報道,也是對事不對人,都是經濟報道,不用投入情感,頂多是一聲嘆息。
自從去了黃島,我發現自己的神經并不是那么堅強。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社會新聞報道,當你面對一個個生命、一個個慘不忍睹的場景時,那種記憶是揮之不去的,因為你面對的不再是受賄的數字和常見的落馬故事。在我看了同事羅潔琪寫的《記者的心債》后,看到這些弱勢而無望的人群,更是不想再挑戰自己做社會新聞調查記者了,盡管我一向尊敬他們。
11月22日-23日:奔赴現場
2013年11月22日,星期五是我們發完稿后最輕松的日子。晚上6點編輯給我電話,黃島死亡人數快40了,太重大了,必須馬上去現場。
之前我的同事龐皎明已經乘坐高鐵去了青島。我能訂到的最早航班已是晚上9點多,到達機場登機口,有幾個黃島當地人在談論爆炸。他們讓我看了手機上傳來的照片,比預想的要嚴重。
從青島到黃島走高速,大約一個小時,連個路燈都沒有,出租車司機已經習慣了這樣在高速上飛奔,最后還熱心地讓他的朋友發來一些現場照片給我看。
第二天早上7點,我和皎明打車到現場,滿眼都是掀起的石板、東倒西歪的車、破碎的玻璃、開裂的樓房。最讓我難忘的是齋堂島街糧油店門口,送貨車的被砸,糧油店的夫婦去搬貨而被砸死,車上還散落著掛面,地上是一灘血跡,還有帽子、馬扎、鞋。越是這些普通的生活場景,越讓人難忘。
齋堂島街的故事,我們做過詳盡報道,這里不再贅述。當我們來到劉公島路路口時,看到中石化的人在做測試,他們往下水道里噴灑大量的白色消防泡沫,周圍的下水道井蓋(青島人叫古力蓋)都是敞開的。我當時的判斷是為了讓里面聚集的氣體散掉。事后才知道有多危險——當晚氣體再次聚集,白天古力蓋被炸開的地方沒事了,但是蓋子沒炸開的地方基本上都有危險,超過爆炸下限的濃度20%,所以才把蓋子都掀開。而皎明一到黃島就先趕赴現場,正是非常危險的時候。
沿著劉公島路往北,越來越接近爆炸地點,但是爆炸點附近百米都被封鎖了,根本進不去。我上到最近的一個居民樓,想俯瞰一下。一上樓,看到好幾家的門敞開著,地上都是碎玻璃,衣柜門都震歪了,停水停電。
走進一戶人家,男主人說,他在爆炸前兩分鐘開車從劉公島路穿過,當時看到他們基本上把路面的油收拾干凈了。“當時有火花,否則怎么爆炸的?”但堵漏應該在地下,他怎么看到的?只有一個信源還是不敢采用,調查結論出來才知道確實如此——“原油泄漏后,現場處置人員采用液壓破碎錘在暗渠蓋板上打孔破碎,產生撞擊火花,引發暗渠內油氣爆炸。”
出乎意料的是,男主人說可以開車帶我們去海邊。當時周圍亂糟糟的,一些路段交通封鎖,也很少有出租車過去。他居然請我們去他喜歡的小飯館飽餐了一頓,又開車送我們到了海邊,真是遇到好人了。原來他是一個做石油物流的小老板,對這里很熟悉。以他聽到的情況,麗東化工廠里確實出事了。
慘不忍睹的海
當我走近海邊的時候,嚇壞了。海上飄著層層油花,蓋著一片片白色的東西,與海水的顏色形成鮮明對比。詢問之后知道那叫吸油氈、吸油毯。附近還有兩卡車這種白色的東西,等待投放下去。地上還放著幾十桶除油劑。
堤壩大概有十米高,環衛公司的工人們把一桶桶除油劑用繩子送到下面的船上,船往海里開一段,投放之后再回來拿新的,完全是人工操作。另一艘船上,有人站在船頭用管子往海里直接噴灑除油劑,大量的化學品被投放到海里。在圍欄外的很遠處,依稀還可以看到船只,污染面積可不只他們說的兩三層圍欄這么近,這次的調查報告亦稱“膠州灣局部污染”,而泄露的原油竟達2000噸!
我從來沒看到過海被糟蹋成這樣。
現場的工作人員說,海事局的人負責清理溢油。兩個海事局的人在車里坐著,說明是記者后,一個人居然下車接受了我的采訪。他說海事局是7點才接到化工廠的報告,并指著高高的照明燈說,你看都被燒成黑的,遠處的航標燈也燒黑了。
“如果你想知道當時發生了什么,你可以沿著堤壩走到入海口,就什么都知道了。”他補充說。
我和皎明就往入海口走。這個暗渠的入海口往北,有大概200米長、10米寬的狹長堤壩,之后才流入寬敞的海域。這個喇叭口里,工人們在加筑堤壩,用石頭和塑料布等從外面包嚴實。
入海口的景象更是驚人,海水又黑又臟,每隔十來米圍有一個護欄,兩邊的堤壩都被燒黑了,石塊上還有深深的油漬,泛著汽油味。
按照安監總局1月11日公布的《山東青島黃島中石化特大爆炸案調查報告》中說法,凌晨4時中石化青島站就安排人員拉運物資清理海上溢油,4時10分至5時左右,開發區應急辦、安全監管局、環保分局、市政局及開發區安全監管局石化區分局、黃島街道辦事處有關人員先后到達原油泄漏事故現場,開展海上溢油清理。8時18分至27分,青島市政府總值班室才電話調度青島市環保局、青島海事局、青島市安全監管局,要求進一步核實信息。
海上溢油主要是海事局負責,需要船只來圈起圍欄,或許當時中石化能做的只是在入海口附近圍上幾道圍欄,根本就擋不住這么大的泄露量。
我們可能是最早來到海邊的記者,拍了很多照片和視頻傳回去。這一路上,我們都是邊用微信的語音功能,把現場狀況口述回編輯部專為報道設立的微信群,邊用手機拍攝現場照片也發回微信群,再由北京編輯部的同事將口述整理成文發稿,配以現場圖片上網。除了我們有三名到黃島的記者,后方還有兩名同事專門整理我們的口述報道,四名記者負責收集整理背景資料,做后方采訪,五名編輯輪班指揮,財新網的后期編輯和技術編輯也一直在值班接力,保證我們的報道能迅速及時發到財新網上,并制作了青島爆炸事故大事記時間軸、爆炸現場圖解等新媒體產品。可以說,這是一次以新媒體手段進行突發事件團隊報道的典型實驗。
麗東化工廠發生了什么?
當我們從海邊往回走的時候,經過麗東化工廠北門。當時網上傳爆炸地點在工廠南門,但并不知化工廠里面到底發生了什么。不過,剛才我們從這里經過的時候,看到十幾輛轎車開進廠區,顯然是工作組的人。這里一定發生了什么。門衛幫我們聯系一個高管,但沒人接聽電話。
我們往前走,看到另一家化工廠里面也搭起了吊車,不知在做什么。正想往里走,一個警察騎車過來說:“這個廠什么事也沒有,你們要是繞到麗東的南門,和那里的工人聊天,就什么都知道了。”
顯然他在暗示我們,里面發生了爆炸。“管道是從廠區外面還是里面走的?”“從里面穿出來的。”又遇到了好人。
但是我們走進南門的時候,又被封鎖住了,門口也沒有人了,只好離開。附近街道都被交通封鎖,我們只能走回爆炸點的最南邊才能打到車。后來看報道才知道,這條路有5000多米。我們返回時走了劉公島路的另一側,就是益和電氣這邊,比來時看到的景象更慘重。
打上一輛黑車,我已經累極了,手機也快沒電了。剛到賓館就接到舒立電話,讓我們把爆炸的這些街道畫個圖發回去。好在皎明是技術高手,拍照時都打開了GPS定位,可以準確地知道位置。后方的技術編輯在我們CTO黃志敏的帶領下,在網上推出了頗具特色的互動地圖。
休息了一個小時,趕赴醫院。當時好像有四家醫院接收現場的受傷人員,其中一家是人民醫院,直覺判斷這個應該是規模比較大的,采訪機會會比較多,直接打車到那里。
住院樓外面有兩個人聊天,他們告訴我這里有現場送來的,但是幾乎每個人身邊都有政府派的人陪著。我想應該是外科和骨科的人比較多,直接上了七層外科。一下電梯就看到三個警察圍著一個小伙子,一看就知是記者被攔住了,我便格外小心。
這個醫院確實很大,一層的走廊很長,中間是護士值班臺。我走到最里面,輕聲地問“有沒有從現場送來的?”一是不能打擾他們,更主要的是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敲了一個個門都沒找到,馬上就要走到護士值班臺了,還是進去吧。
“有沒有從現場送來的?”沒想到靠里面的就是,而且是麗東化工廠出來的,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直接便問化工廠里爆炸了嗎?他說自己所在的簡易工棚正好在管道上面,死了5個,早晨才被挖出來,其中一個姓管的年紀很輕,我后來在遇難者名單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這位受傷者是輕傷,所以才能和我講半天。他39歲,講話很靠譜——講的很多細節后來證明都是對的,而且講話很生動,“就幾秒鐘的時間,砰砰砰,比放鞭炮還快,沖擊波把我彈到一邊。”他的妻子也非常好,說當地人對化工廠都很反感。
看了調查報告才知道,他們建在管道上的簡易工棚是違章搭建,政府部門失察。
談了幾十分鐘都很順利,最后想翻拍他手機上的一張現場照片,得把手機放在屋子中間燈下的亮處。很快外面進來一人,“這是干什么呢?”
我把手機放回他床頭的桌上,馬上離開房間,他跟了出來,一直跟進了電梯,問我是干什么的。我當時很氣憤,“你干什么的,你一個便衣還問我?”(后來想這個50歲左右的男人也可能是工廠派來的)他探頭想看我的手機,我當然不能給了,里面存了那么多照片。
從7層下來,時間有點長。“我聽說這里有現場送來的,想拍點照片,怎么了?”“沒什么,沒什么。”他趕緊說。我一走出電梯就看他拿出手機,距離大門還有百米,有點長,沒人阻攔,徑直走出打車離開。
回到賓館,快速整理發稿。已是后半夜,皎明還在整那個復雜的地圖,同事們還在微信群里熱烈地討論著下一步報道計劃。
11月24日,我從上海增援過來的同事謝海濤,趁晚上保安松弛,摸黑進了麗東化工廠。工廠很大,晚上又黑又冷,他走了很遠,堅持找到了那片倒下的工棚。他可能是唯一或少數真正進入爆炸地點和化工廠爆炸現場的記者。
11月25日:都不吭聲
我通常起的比較早,看到7點北京的同事就開始工作了,想再睡會兒也不好意思了。今天要去政府部門,第一個要去的是管排水管道的市政公用局,了解輸油管道為何能穿過暗渠,而不是封閉的。
市政公用局在新建的政府大樓2層,周日沒有人,辦公室的人讓我去指揮部找黃島負責宣傳的人。我正想進指揮部呢。這個指揮部就在黃島石化安監分局,樓很新,2008年初才開建的,但門口有士兵把手,就是當地工作人員也得有特殊證件才能進去。
之后又去環保局、消防大隊等地,但相關的人都到指揮部去辦公了,根本采訪不到人。好在北京的同事獲悉了調查組所在地,就在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青島校區邊上的黃島藍海金港大飯店。
上午調查組在一層開會。結束后堵上一個調查組的人,他是查規劃的,但是讓當地政府提交規劃原圖,也沒提交上來。之前,青島市政府副秘書長郭繼山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過:“黃島管線情況非常復雜,至少鋪設了11條各類管線,較擁擠,部分管線有交叉。”這11條線的圖規劃局應該有,但他們說都送走了。連負責管道建設和運營的人也不敢說話。
在酒店的一層有幾個中石化的工作人員,在準備接待來自徐州、北京等地的人,因為中石化管道儲運分公司的總部在徐州。他們說準備在這里待一個月。這些人不停地開會,也請來專家給他們分析事故原因。這次被認為對事故發生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管道公司副總高安東在電話里說,他還在現場。
這幾日,黃島每天都至少舉辦一次新聞發布會,筆者只參加了最后一次。發言人幾乎沒有回答大家的提問,甚至就一些基本事實也不作答。在場的記者們反復詢問在這7個小時里政府做了什么,他們總是說下次回答。
11月26日 搬遷訴求
今天,黃島的情況陡然生變。據說前一天晚上,黃島區政府部門的兩個人被帶走了(其中一個就是開發區安全監管局副局長兼石化區分局局長任獻文),當日下午我再次去政府大樓時,氣氛已經完全不對了。
大家知道,很多地方新建的政府大樓都很氣派,前面有碩大的草坪。黃島區政府的辦公大樓也不例外,大概得有一百多米長。樓前面站了一排警察,每隔不到兩米就站一個,門口停著一輛公安的大巴。樓內每層都有保安。出來后,路邊上也是一堆堆的警察。
馬路對面站著三排警察,原來是有上訪的民眾。有個頭上纏著白布手里拿著材料,他是為以前的冤案來的。
另一堆是爆炸點附近小區的居民。只聽一位男士說:“你們可以打橫幅,打十分鐘沒關系,完了就回去吧。”我找到其中一位看上去像是帶頭的人,她看了我的記者證后,叫來其他幾個人,和我講了他們的訴求,就是要求搬遷,不能再在這個石化島上住了。
“化工廠搬遷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搬我們搬。”他們說。
把采訪內容語音用微信傳送過去后,后方值班的編輯快速整理出文字,再貼在微信群里,我當場回復幾處小的修改。這時,聽見有人說一個男孩被帶走了,我不能再等了,必須得拍照片了。我走過去的時候,他們正準備開始打橫幅“黃島人民強烈要求搬遷”,喊出的口號是“我要活著,我要搬遷”。
還有些圍觀的人在拍照,所以我拿手機拍照并不特別起眼。看到這些勇敢的黃島人,深受鼓舞,他們都不怕,我怕什么?走近人群,“搬遷”兩個字突顯在鏡頭中。
拍完后離開仍在喊口號的人群,忍不住哭出了聲:“我要活著,還有錯嗎?這世道!”
一個也來到現場的《中國青年報》記者認出了我,說里面有宣傳部的人。我又不是壞人,我怕什么?
我們的現場報道出來得很快。看到同事們在微信上說,有個讀者在文章下面留言,說是聽說有人抗議,剛想下樓就看到財新的報道,贊揚“財新速度”。我們的一位編輯說,不管我們的文章藏的多深,想看的都會看。
當晚居民們告訴我,黃島區委書記在區政府大樓門口的會議室見了當天去的六七十人,說是給一個月的時間去小區調研。據說第二天又去了200多名居民,一個副區長徂徠接待,說政府把善后處置完了,轉過身來就考慮這個問題。
當天的氛圍很奇怪,以前已經開放的幾條爆炸街道又攔起來了,新聞發布會也不再開了,很多記者被單位叫了回去。有記者告訴我,他們在黃島的時候就整天被宣傳口的人跟著,在酒店下面等著和你一起出去。
第二天,27日,現場指揮部就公布了改道的消息:東黃輸油管道黃島泄漏段線永久停用;秦皇島路、劉公島路現有全部石油和化工管線遷至北部遼河路化工專用通道;劉公島路至入海口段排洪暗渠改建為生態休閑景觀明渠,具體方案將按規定公示,征求廣大市民意見。
當地一位政府部門的官員說,這個改道的決定和上訪不無關系,可能以前有這個想法,上訪加速了出臺。但是附近業主仍表示:“輸油管道只是引信,化工廠才是炸藥包,現在把輸油管道移到北邊的遼河路上去,是覺得這次死人少了!”當然,我們發表的時候把最后一句話改的更緩和。
但是到現在,一個月早就過去了,也沒說法。當地的一個居民說,樓都有裂縫了,還說不是危房?他們光把門窗修好管什么用?(財新網)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