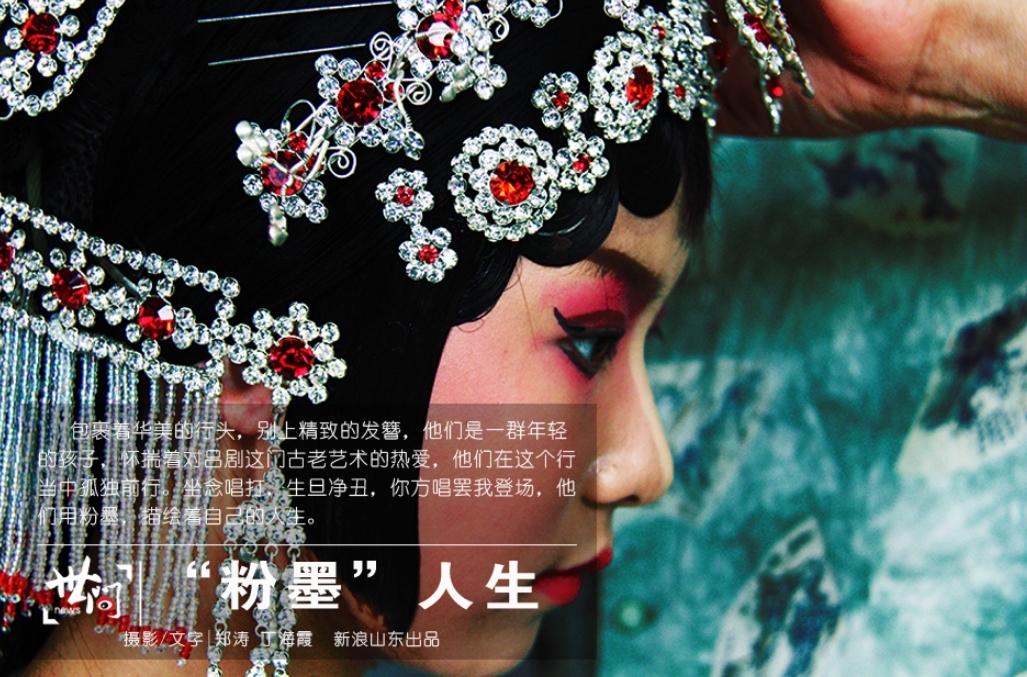骨刻文守望者丁再獻
骨刻文守望者丁再獻 丁再獻用骨刻體手書“中國夢”
丁再獻用骨刻體手書“中國夢”
聯合日報2014年7月7日第3版
記者:岳遠攀/文 王永新攝影
最早的漢字是什么?這似乎不是個問題。甲骨文嘛!但丁再獻給出的答案卻有所不同:最早的漢字是東夷骨刻文。
漢字的產生,目前為止公認且有據可查的乃是公元前14世紀殷商后期的甲骨文。但郭沫若在研究甲骨文以后,推測甲骨文從初創到成熟,起碼要經歷1500年以上。其后的一系列考古證明,這樣的推斷是有依據的。考古學家們也幾乎一致認為,甲骨文絕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
“常說中華文明5000年,但甲骨文之前卻有1500年左右的空白期,因而有‘有商周而無夏’的疑問,骨刻文的發現卻補全了這5000年。”2010年,山東省旅游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東夷文化學者丁再獻接觸到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所長劉鳳君教授的骨刻文考古發現與研究后,不僅破譯了數百個骨刻文字,并且大膽提出:山東是東夷文化的發源地,東夷人首先創造了骨刻文字,很可能是漢字的源頭。
破譯東夷骨刻文
考古研究證明,東夷文化從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開始,歷經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前后跨越5000余年,是以山東為發源地的中國古代文明,也是華夏五千年文明發展的源頭,而一直沒有間斷。“昌樂、龍山、壽光發現的近萬塊獸骨可佐證,東夷文化的發源地在山東。”丁再獻說。
何為骨刻文?顧名思義,就是刻在獸骨的文字。作為文明產生的標志,東夷骨刻文既是東夷文化的載體和精髓,也是打開東夷文化大門的鑰匙。據悉,2005年,劉鳳君在濟南收藏家手里發現一片有刻劃的骨頭,2007年又在昌樂縣、壽光市、章丘市等地集中發現,肖廣德等收藏家也發現了許多重要的骨刻原件。劉教授考證這些骨刻文距今4600年至3300年之間,是龍山文化時期流行的文字,最后將其定名為“骨刻文”。
最大的難題在于,這些骨刻文字如何解讀和辨識。據悉,自2008年起,劉鳳君先后發現了堯、舜、龍、鳳、鹿、豕、犬、人等八個象形字,由于沒能書寫成文,對此有人提出質疑,認為佐證太少,甚至給予否定。
2010年9月,潛心研究東夷文化的丁再獻,登門拜訪了劉鳳君教授。而這一次會面,讓丁再獻與骨刻文一見鐘情,此后便一發不可收拾。“劉教授家里,陽臺上滿滿地放著數百塊骨頭。當時在很多人甚至考古學家眼中,那就是一堆‘爛骨頭’,全盤否定劉教授的骨刻文字說,但我學了三十多年的書法,當時乍一看那些獸骨上面刻著的圖文,憑借多年書法、篆刻和古文知識的累積,一下就看出那的確是文字,而非‘蟲咬草腐’。”丁再獻說。
通常認為,漢字的造字法首推象形,而象形起源于事物形象的摹畫,骨刻文恰好處于形象摹畫向文字符號過渡的歷史階段,也正是漢字的象形文字形成的初始階段。因此,丁再獻大膽推斷,距今4600年到3300年的東夷骨刻文就是漢字的源頭,其晚期與甲骨文形成的早期交叉使用。在丁再獻看來,劉鳳君對于東夷骨刻文的發現,是繼100多年前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以來,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發現,“可稱得上當代王懿榮了”。
懷揣著對東夷文化的追逐和對書法藝術的熱愛,丁再獻開始了對骨刻文艱苦細致的研究,他把旁人眼中的“爛骨頭”當成了寶藏。丁再獻戲稱自己是“一無門派、二無名校、三無學術頭銜” 的三無業余研究者,有幸加入到“猜謎游戲”。但僅用了半年,他就從手中130多件骨頭上的文圖中破譯了100多個字,而后家兄丁再斌又破譯出50多字,這樣到2011年底就破譯出了200多字。
解說旅游中國夢
首先系統破譯并始創了東夷骨刻文字書寫藝術,丁再獻并不滿足,也十分關注骨刻文字如何釋讀的問題。“現在,家兄丁再斌已經破譯出200多字,加上我破譯的一部分總數已達到400字之多。家兄丁再斌是研究古漢語言文學的專家,我在書法上僅算有點長處,但文字解讀上就主要靠他了。”丁再獻說,通過哥倆對骨刻文字研究發現,以前的一些字的解釋并非全部準確,甚至有的風馬牛不相及。
在丁再獻的辦公室,墻上掛著很多他的骨刻字書法藝術作品。其中一副“中國夢”三個字尤為顯眼。他說,古人解釋“中”字一為上下貫通;二像旗幟,中為旗面,上下曲線為飄帶,旗桿正中豎立,這種解釋多少年來無人懷疑。試想,旗子飄揚時只有飄帶擺動而旗面能不擺動嗎?丁再獻研究發現與壽光32號-127圖一幅兒童抽打陀螺的骨刻圖有密切關系,圖中一個兒童正在用力甩鞭抽打著類似陀螺的物體,陀螺轉動時的位置就是中心,東夷人可能將重心作為中心,這可能就是最初“中”字的啟蒙。所以甲骨文和金文“中”字的形狀與骨刻文圖幾乎一樣,原來“中”字出于陀螺原型,陀螺上下的曲線正是陀螺轉動時的動感線,而不是什么旗幟飄帶。“如果許慎看到這幅‘兒童與陀螺’骨刻文圖的話,起碼會認為原來喻旗的解釋欠準確。”
每寫一幅字,丁再獻都需要先從獸骨上的圖臨摹下來,再將其規范寫成骨刻文,接下來依照骨刻文、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的順序,用五種字體勾畫出不同時期文字的演變過程。這是相當枯燥的破譯過程,但對于丁再獻來說,這種枯燥微不足道。每一塊獸骨在丁再獻的眼中都充滿無窮的魅力,他把常人眼中的“亂麻”解讀成一個個美麗的故事。
“我反對將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丁再獻說,祖先發明文字的用意很簡單,每一個文字符號的產生,都是一種最直白的表達。比如“夢”字,家兄丁再斌解釋:在骨刻文的寫法中就是一個人側身睡覺時,夢見兩人在其床上跳舞,后來人們將其側身睡覺的姿勢寫成夕陽的夕,表示天黑了,表達的意思非常形象。鑒于對古文字的這種理解,丁再獻的研究愈發生動而有說服力。
2012年2月,丁再獻歷時近10年多90萬字的《東夷文化與山東•骨刻文釋讀》新著正式出版。該專著是我國第一部全面論述東夷文化、追溯中華文明源頭的力作,被譽為劃時代的文化巨著、東夷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引領者和導航儀。其“骨刻文釋讀”一章,列舉了一批東夷骨刻文的破譯和解讀,為東夷文化源頭論提供了有力佐證。
說到《東夷文化與山東•骨刻文釋讀》的成書,丁再獻家兄丁再斌表達了發自內心的敬佩,他說:在我的心中,家兄丁再斌是偉大的。當文稿送到家兄案頭后,他并未表示滿意,不僅提出了不少意見,而且進行了大面積的修改。當第五稿寄回后,已經條分縷析耳目一新了。有不少章節已經基本反映了家兄的研究成果,他的很多觀點貫穿了全書。《骨刻文釋讀》一章也是如此,其中50多個會意字、假借字全是家兄的破譯和解讀,就連我解讀的一部分也是經過家兄潤色,才有了高層次的提升。可以說,家兄對該書成敗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沒有家兄的努力,也就沒有今天的成果。而家兄不為名、不為利,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丁再獻說,東夷文化仍然是一片充滿懸疑的陣地,嘲諷、不屑、流言蜚語,一刻都未曾停歇。但是,他的努力終于引起了學界和政府部門的重視和肯定。2013年6月,《東夷骨刻文研究與利用》正式通過山東省重大課題立項;2014年1月,省文化廳決定實施“東夷文化溯源工程”,對于丁再獻和堅守在東夷文化陣地的為數不多的學者們來說,這是足以令他們振奮的消息。
“旅游中國夢,好客山東人。”這是丁再獻辦公室的另一幅骨刻文書法作品。骨刻文的系統破譯,骨刻文書法藝術正式創立,漢字在這里起源,已經成為山東又一張嶄新的名片,不僅是對我省文化事業的一大貢獻,也必將成為一種嶄新的、重要的文化旅游資源,必定會吸引眾多的中外客人到中國漢文字發源地親身體驗。丁再獻說,省旅游局也十分重視東夷文化與旅游開發研究,非常看好東夷骨刻文字旅游開發的前景。
“東夷文化的核心地區---山東,一定會成為中國人尋根問祖的目的地。骨刻文字發源于山東,也一定會在中外產生巨大影響,為人類文化研究做出不可估量的貢獻。”祝愿這位謙虛、敢講真話的東夷骨刻文守望者,早日實現他的中國夢,以及齊魯大地的旅游中國夢。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