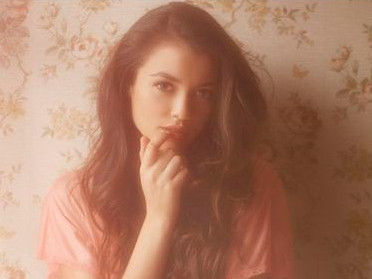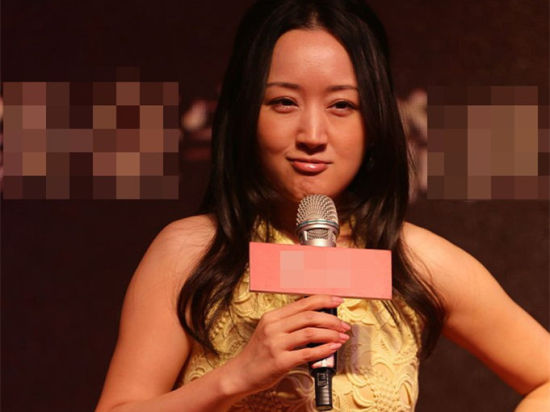毛新宇新書《母親邵華》封面(資料圖)
毛新宇新書《母親邵華》封面(資料圖)人民網北京12月30日電 (陳苑)毛澤東唯一嫡孫毛新宇將軍的新著《母親邵華》,近日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毛新宇將軍回憶其母邵華的深情大書。作者分別從母親邵華早年的坎坷經歷、母子之間及親人之間的相處、母親的處世風格、母親對攝影的熱愛四大部分講述了共和國女將軍邵華的一生經歷。毛主席曾以父親的名義題詞:少華是個好孩子。第一紅色家庭的種種顛簸過往,辛酸苦辣,平淡幸福,在書中徐徐展開。
毛岸青夫妻一起到棉花坡祭奠楊開慧
在總參陪同人員的護送下,他們首先回到長沙。他們已經九十高齡的外婆耳聰目明,身板硬朗,記憶力特別好。她一手拉著外孫,一手拉著外孫媳婦,端詳來端詳去,看到自己昔日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的小伢崽,如今長得高大魁梧,而且還帶回個修長大方、善解人意的媳婦,半天舍不得松手。老人經歷了清末、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時代,眼見滄海桑田,親歷天翻地覆,自照顧爺爺在長沙上學到撫育她的三個外孫,關愛了兩代毛家人。如今老人到了耄耋之年,女婿開天辟地,萬民敬仰,外孫久別歸來,外孫媳婦翩翩而至,人生在世,福祿壽禧,四喜登門,還有什么不稱心的呢!
在板倉的日子,母親詳細地察看了開慧奶奶的件件遺物,詢問了奶奶犧牲前的經過,又和父親一起到棉花坡祭奠了奶奶。在墳前燒了紙,給墳添了土,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了外婆家。
父親和母親回韶山的消息一傳開,十里八鄉的鄉親都趕了過來。
毛氏家族的后裔來了,爺爺親自建立的韶山黨支部的老黨員來了,跟隨爺爺打天下的烈士親屬來了,戴著紅領巾的少先隊員來了。人們并不在意父親和母親說不了家鄉話、搞不清輩分高低、吃不慣烈辣的飯菜。濃郁淳樸的親情鄉情,難忘的烽火歲月,讓人們圍攏在一起,說毛家的故事,說家鄉的收成——他們為韶山出了個毛澤東而驕傲,為爺爺重古崇禮、派兒子兒媳回家認門而嘖嘖稱道,更為毛家人丁興旺、后繼有人而衷心祝福。
這樣的場面,讓人們不禁想到1959年6月25日爺爺回韶山那激動人心的情景……
母親邵華參加“四清”運動 聞著豬圈的氣味度過了一個夏天
1965年年初,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先為“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后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各行各業均抽調部分人員輪流下放農村指導工作。
4月底,母親隨北大中文系赴湖北江陵農村參加“四清”。工作組坐火車到武漢,換乘江輪到江陵,然后徒步翻山越嶺趕到目的地。那時的江陵人多地少,經濟落后,交通不便,疾病頻發,生產生活條件依然艱苦。
母親的房東是個寡婦,帶著兩個五六歲的孩子過生活。家有坐北朝南的三間木板房,中間是堂屋灶屋兩用。房東住西屋,母親住東屋,臥室沒有窗戶,依靠堂屋的大門采光。堂屋比較大,供著灶火神,擺放著簡陋的飯桌和簡單的農具,與堂屋一板之隔的后方是豬圈。
大概是孤兒寡母無能為力的緣故吧,板墻既沒用磚砌也沒用泥糊,堂屋與豬圈之間露著很大的縫隙,所以豬圈有多臭屋里就有多臭。開始時母親聞著豬圈的氣味感到頭暈氣短,寢食難安,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就在這樣的環境里,母親度過了整整一個溽熱的夏天。
房東是一個很能干也很爭氣的婦女,她起早貪黑,特別能吃苦。但由于身單力薄,農田里的許多農活還是趕不上別人。母親雖然沒有從事農業生產的經歷,但也是個從小吃過苦的人。兩個在性格脾氣上有不少相同之處的女人在一起,同煮一鍋飯,同挑一缸水,同耕一片田,使先前凌亂的家煥然一新,兩個小孩子也有了歌聲和笑聲。
但這還只是母親工作的一小部分,她是這個新家里的主要勞動力,絕大部分時間是下田插秧、渠灌、施肥、拔草和割稻打場,成天是放下鋤頭拿起镢頭,沒有節假日,唯有大雨滂沱時才能休息等于老天給放了假。但夜晚還要參加工作組討論會,開辦農民夜校,學習研究和推廣快速積肥、科學種植、改良土壤、增產增收等農業新知識新技術。所以,從時間上來說,母親基本上是臥倒就睡,睜眼就干,除了抽出時間寫日記,沒有其他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日子過得很有意義也很充實。
爺爺毛澤東專門抽時間聽母親邵華的“四清”匯報和體會
實踐出真知。母親初來時,挑水挑半桶,不會使用農具,到后來了不歇氣能挑五六擔水,各種農具也使用得得心應手。通過勞動,她從農民那里學到了許多課本上學不到的知識,當地的歷史、地理、氣象、土壤、植被、作物、特產,甚至疾病和災害預防,都列入到了她的視野范圍。農村的生產關系、生產資料、生產成本等,也同樣給她帶來了新的研究任務。學習中文的母親來這里經歷了一次思想上的質的飛躍。
江陵農村地少路窄,獨輪車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和日用農具。剛開始,母親一次只能搖搖晃晃地推起二三十斤重的東西,而且時不時地連人翻倒在田埂下。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她慢慢也能推起百把來斤了,最多時能推到了二百多斤,獨輪車在田埂上走得穩穩當當。一次,暴雨襲來,因田埂又窄又滑,她一腳踩滑了,連車帶人翻進了稻田,造成胳膊肘脫臼,不得已提前十天左右回京治療,結束了她長達半年的農村生活。
母親回京后,爺爺專門抽出時間聽了她的“四清”匯報和體會,而且還問得很詳細。他問母親是怎樣開展農村調查的,與多少群眾交談過,農民對黨的政策有哪些意見和建議,水稻的畝產量有多少,上交公糧賣了余糧還剩多少口糧。還問到農村孩子的上學、江陵的風土人情等情況。最后,爺爺又語重心長地說:
“很好啊,不吃梨子,哪能知道梨子的滋味。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占大多數,不了解農民,不發展農業生產,誰坐在北京也是空著急。黨政領導干部只有深入農村,才能制定出一套好政策。‘沒有大糞臭,哪有五谷香’,事物的道理就是這么簡單,有的人卻看不起農民。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不是嗎!怎么樣?下田干活不像舞臺藝術那么夸張吧?‘書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看是很有道理的。以后,有機會你還要去拜他們為師,取他們的真經!”
母親把爺爺的話認真地記在日記本上,也珍藏在了心中。許多年過后,她再三咀嚼著爺爺說的話,越發覺得意味深長。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
中國潮人怎么玩游艇